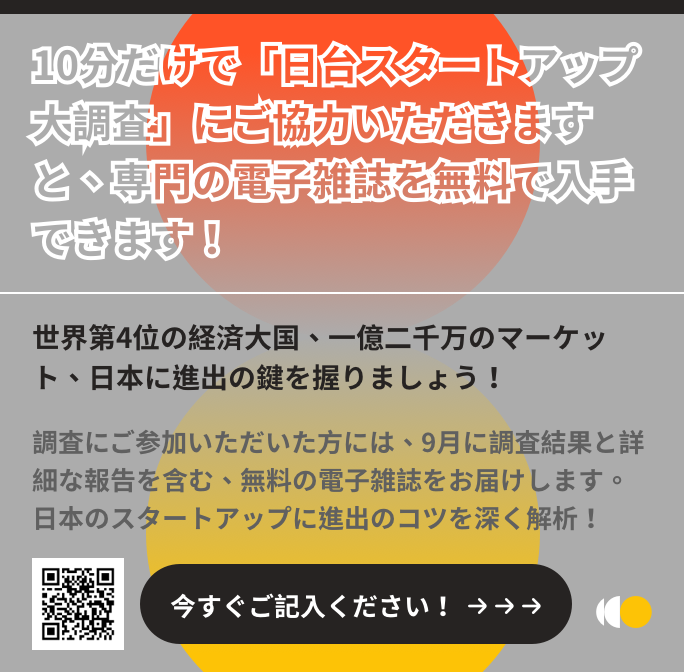如同歷史上所有抗議行動,目前蔓延全美超過 80 所大學的挺巴勒斯坦學潮,是一場關於如何理解、如何記憶的抗爭。
在許多人眼中,衝突始於 2023 年 10 月 7 月。那天,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突破加薩邊境隔離牆,對以色列發動襲擊,造成約 1,200 人死亡,並綁架了 253 名人質,其中多數是平民。以色列隨即展開反擊,全面加強對加薩走廊的軍事行動和封鎖。根據加薩走廊衛生部的統計,截至 2024 年 5 月 2 日,以色列已造成 34,596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平民同樣占多數。
迅速累積的傷亡人數,震驚了國際社會。一名聯合國特別報告員於 3 月 26 日人權理事會上表示,目前已經有「合理的根據」,相信以色列在加薩犯下了「種族滅絕」(genocide)的罪行。這個極具爭議的詞彙,也見於近期的美國學潮,學生吶喊著「立刻停止種族滅絕」、「停止資助種族滅絕」。
與之相對的,是美國媒體《The Intercept》於 4 月 15 日披露,根據一份流出的《紐約時報》內部備忘錄,報社高層要求記者在報導以色列─哈瑪斯衝突時,不要使用「種族滅絕」、「種族清洗」等詞彙。並非所有記者都同意這個指令,《紐約時報》耶路撒冷分部陷入激烈爭論。
此處的問題是,以色列去年 10 月至今在加薩的軍事行動,算不算「種族滅絕」。這是關於我們該如何理解、用什麼語言去理解的抗爭。
但爭議不僅於此。在 10 月 7 日的哈瑪斯襲擊、在至今超過半年的以色列軍事行動之外,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們,還要求人們看見衝突的根源,即 75 年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佔領和壓迫。
「猶太和平之聲」(Jewish Voice for Peace,簡稱 JVP)成立於 1996 年,是美國最大的、以猶太人為主體的反錫安主義(anti-Zionism,Zionism 又譯「猶太復國主義」)行動組織,在全美各大學設有分部,是這次學潮的重要組織者之一。
在去年以哈衝突爆發的當下,猶太和平之聲就發表一篇名為〈暴力的根源是壓迫〉的聲明,指出「75 年來,以色列政府一直對巴勒斯坦人進行軍事佔領,實行種族隔離制度」,「今天(按:指 10 月 7 日的哈瑪斯襲擊)和過去 75 年的流血事件,能直接追溯到美國在以色列軍事佔領造成的壓迫和恐怖中,所扮演的共謀角色」。這是關於我們該記得什麼、如何記憶的抗爭。
猶太和平之聲於是呼籲美國政府應立刻採取措施,撤回對以色列的軍事資助,並追究以色列政府侵犯人權的戰爭責任。「我們承諾升級我們的抵制、撤資和制裁運動,以結束數十億美元從公司和私人基金會持續湧入以色列戰爭機器。」聲明如此作結。
如今蔓延全美校園的挺巴學潮,在立論和主要訴求上,都延續了這則聲明,只是把呼籲對象從政府換成校方,以及在「抵制、撤資和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s,通常簡稱 BDS)中強調「撤資」,再加上一個「揭露」(disclose),要求校方揭露數十億甚至數百億美元的捐贈基金投資組合中,究竟有多少資金流向和以色列軍方有關的公司,停止這些投資。
作為檯面上的核心訴求之一,「撤資」的相關討論已見於不少國內外媒體。因此,在觸及作為以巴問題核心的記憶政治之前,得先回答一個問題:要求校方從以色列撤資,真的有效嗎?
撤資訴求在經濟上有問題,但問題不在經濟
答案是:從經濟角度來說,小規模撤資無效,大規模撤資幾乎不可能發生。
小規模撤資指的是大學從以色列公司撤資。但由於許多以色列公司都是良好投資標的,一旦大學捐贈基金撤出,其他資金會立刻補上,對以色列幾乎沒有影響。
而事實上,根據《華盛頓郵報》的研究,美國最大的幾所公立學校的捐贈基金,只持有非常少的以色列和美國國防股票(私立大學不需公開資金流向,因此無法調查)。沒有投資,要怎麼撤資?「這凸顯了抗爭者對於撤資的要求根本難以被滿足。」《華盛頓郵報》指出。
大規模撤資指的是大學從所有和以色列軍事行動有瓜葛的公司撤資,這可能包含武器製造商、為以色列佔領區提供基礎建設和監控技術的公司,甚至擴及所有和以色列政府有合作的公司,如 Alphabet、Amazon、微軟等科技巨頭。這樣一來範圍就很大了,如果連透過指數型基金(ETF)觸及的狀況都考慮進來,那不論目前的投資組合為何,校方勢必得做出極大調整,甚至面臨沒東西可投的局面。對管理鉅額資產的大學來說,這顯然不太實際。
《經濟學人》近期就語帶諷刺地指出,要求撤資的抗議學生對金融市場有著「神奇的思考」,由於三分之一的常春藤畢業生會進入金融或諮詢領域工作,了解金融市場的實際運作,「可能對他們其中的一些人未來的職涯有幫助」。
以上評論都說得都對,但認為抗議學生缺乏金融常識、搞不清楚狀況,恐怕也只是某些英美主流媒體一廂情願的想法。
《旭時報》作者謝達文在近期一篇刊登於《端傳媒》的文章中,同樣指出撤資一類的杯葛運動,對以色列經濟其實影響不大。然而,示威的目的其實不是要促成對以色列的經濟制裁,而是藉由點名一間間應該被抵制的公司,來傳達政治、道德訊息,讓世人注意到以色列政府對巴勒斯坦人的長期壓迫。
謝達文寫道:「(BDS 運動)透過一個又一個案例,不斷向外界傳達『以色列的政策涉及根本的不正義』,而且主張這些不正義並不只關乎眼下是否有戰爭的問題,也不只發生在約旦河西岸等佔領區,更發生在以色列境內,是因為以色列堅持自己是猶太人國家,於是持續把巴勒斯坦/阿拉伯裔公民當作次等公民,與當年的(種族隔離的)南非屬於同一類別。」
以「布朗大學撤資聯盟」(Brown Divest Coalition)今年 2 月發布的報告為例。這份報告一共點名十間公司,以下是其中四家:
- 波音(Boeing):美國飛機製造商,為以色列國防軍提供炸彈、戰鬥機和其他軍事技術。
- 通用動力(General Dynamics):全球第六大軍事公司,為以色列軍方提供武器。自去年 10 月 7 日以來,以色列軍方用得最多、威力最大的 MK-84 炸彈,就出自通用動力公司。《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指出:「在加薩戰爭的前六周,以色列經常在其宣布為平民安全避難區的地方,使用其最大、最具破壞性的炸彈之一。」
- 富豪集團(AB Volvo):瑞典汽車製造商,為以色列監獄管理局提供巴士,用於運送巴勒斯坦政治犯;為以色列提供重型機具,用於建造檢查哨和隔離圍牆。
- 摩托羅拉系統(Motorola Solutions):美國電信公司,為以色列提供維護佔領和隔離區的技術支援。2005 年以來,摩托羅拉的 MotoEagle 廣域監控系統幫助以色列維持約旦河西岸佔領區的秩序。
藉由揭露這些作為以色列「共犯」的公司,抗議學生和 BDS 運動的支持者們希望引導輿論,形成道德壓力,使得支持以色列政策成為有爭議的行為。
另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發生在位於紐約曼哈頓上城、讓這波學潮蔓延全美的哥倫比亞大學(以下簡稱「哥大」)抗爭現場。在 4 月 30 日晚間的紐約警察清場中,有人拍到開拓重工(Caterpillar)的挖土機出現在現場。
開拓重工被 BDS 運動列入頭號黑名單。這間美國公司為以色列提供武裝推土機,用來拆毀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公共建築、道路和其他民用基礎設施,拆毀過程中,有時導致平民喪生。2003 年,美國和平運動者科里 (Rachel Corrie)試圖保衛巴勒斯坦人的房屋,被開拓重工生產的 D9 推土機活活輾死。
很難想像當來自巴勒斯坦的抗議學生,在校園看到 CAT 標誌(開拓重工的商標)時,內心感受到的衝擊。出現在紐約街頭的挖土機,讓抗爭現場和加薩走廊有了立即的聯繫。壓迫不再只存在於遙遠的遠方,而是成為近在眼前的暴力。
抵制運動的記憶:以色列是一個「種族隔離」國家嗎?
在了解撤資不(只)是經濟行動,而是希望傳達道德訴求後,我接著想談談這場挺巴抗爭是如何調動包含反南非種族隔離運動、60 年代反越戰學運的記憶,來進行政治上的抗爭,去改變人們理解世界的方式。
一個重要的記憶參照是 20 世紀後半的南非種族隔離(apartheid)體制。事實上,針對以色列的 BDS 運動最初在英國發起,重要的啟發就是 1980 年代的反南非種族隔離行動。運動者試圖傳達這樣一個訊息:以色列作為一個不正義的國家,針對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實施體制化差別待遇,有如當年南非國民政府對白人、有色人種、印度人、黑人的隔離政策。
在先前提及的布朗大學撤資聯盟的報告中,便有一節專門討論當年抵制南非的成功先例。1986 年 3 月,布朗學生在 IBM 的當地辦公室外靜坐抗議,譴責該科技公司參與南非種族隔離體制,要求布朗撤回對 IBM 的320 萬美元投資。幾個月後,在全國學生反對種族隔離的壓力下,IBM 徹底退出南非市場。該年 10 月,美國國會通過「全面反種族隔離法」(Comprehensive Anti-Apartheid Act),對南非實施經濟制裁,最終導致南非在 90 年代逐漸廢除隔離體制。在南非的例子之外,該報告也提供抵制蘇丹政府、煙草公司、化石燃料產業的先例。
走過種族隔離的南非,於 2023 年 12 月 29 日將以色列告上國際法院(ICJ),要求對以色列在加薩的軍事行動立即下達停火令,以防止「種族滅絕」發生。國際法院於 2024 年 1 月 11、12 日舉行公開聽證會,於 26 日下達命令,要求以色列應「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防止種族滅絕發生,但沒有要求停火。哥倫比亞在 4 月 5 日提起同樣的訴訟。
回到布朗大學的這波抗爭。4 月 30 日,布朗校方和示威學生達成協議,校長邀請 5 名學生下個月和負責管理捐贈基金的布朗大學公司(The Corporation of Brown University)的成員會面,提出「從協助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領土的公司撤資」的論點。無論會面結果如何,布朗大學公司都將在 10 月的會議上,對是否撤資進行投票。學生則同意當天拆除校園內的「加薩解放營地」,結束抗爭。
布朗是挺巴學潮在美國全面升級以來,極少數和學生達成協議的大學。有評論指出,這可能只是校方方面的拖延戰術(儘管比逮捕學生好得多)。但考慮以色列在國際社會上,正面臨許多國家的控訴和來自聯合國的壓力,等到 10 月布朗大學公司對撤資進行投票,風向會如何演變還很難說。
即使是最支持以色列的美國政府,也於 28 日遭路透社爆料,指出根據一份內部備忘錄,某些官員向國務卿布林肯表達擔憂,認為以色列使用美國提供的武器時可能觸犯了國際法。5 月 3 日,86 名民主黨議員共同簽署一封致總統拜登的信件,認為以色列正在限制人道援助進入加薩,違反了美國法律。5 月 8 日,拜登承認美國炸彈被用來殺害巴勒斯坦平民,若以色列執意進攻拉法(Rafah),美國將扣留某些武器。
當然美國政府不可能直到現在才搞清楚狀況,發現以色列在加薩的軍事行動可能違反人道法。但此時放出這些訊息,除了以色列的軍事行動真的太過激進外,可能也意味著拜登有意向年輕人示好。根據 2 月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18 至 29 歲的年輕人是美國所有年齡層中,唯一對巴勒斯坦人好感度(60 %)勝過對以色列人好感度(46 %)的族群。隨著年底大選接近,民主黨一方面面臨鞏固年輕選民的壓力,另一方面也必須控制蔓延全美的學潮,避免共和黨操作「民主黨太過基進,導致社會陷入混亂」的指控。

挺巴學潮和 60 年代反戰運動可以相比嗎?
另一個在此次學潮中被調動的記憶,是美國 60 年代的反戰運動。某種程度上,運動者不只對記憶進行抗爭(在當下的以哈衝突外,我們更該看見 75 年來的壓迫),也使用記憶進行抗爭。
4 月 30 日午夜,哥大學生面對校長沙菲克(Minouche Shafik)於前一天表示校方「不會從以色列撤資」,決定升級行動,衝入並佔領漢密爾頓樓(Hamilton Hall),將其更名為「欣德樓」(Hind's Hall),以紀念 1 月份被以色列軍隊殺害的一名六歲巴勒斯坦女孩。
學生之所以選擇佔領漢密爾頓樓,是因為該建築在 1968 年的哥大抗爭中有重要意義。1968 年 4 月 23 日,數百名哥大學生佔領漢密爾頓樓等五棟建築,將柯爾曼院長(Henry S. Coleman)扣為人質約 25 個小時。學生抗議校方在黑人社區興建種族隔離體育館的計畫、大學與國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的聯繫,以及越南戰爭和徵兵制度。
和 60 年代在全美風起雲湧的抗議活動相同,68 年的哥大抗爭混雜了種族平等、女性解放、反對越戰等一系列訴求。其中加劇反戰運動的,是美國政府於 1967 年嘗試修改徵兵法案,讓學生更難透過就讀研究所來申請緩徵,甚至賦予總統推翻年齡排序的權力,要求 19 歲的年輕人優先入伍。這導致美國在 60 年代末出現大量逃兵,年輕人不願意接受徵召,拒絕到越南參與不正義的戰爭。
在抽象意義上,現在發生於美國高校裡的學潮,和 1960 年代的社會運動相比,有著相近的目標:終止遠方的戰爭、廢除種族隔離、結束以美國為中心的帝國主義秩序。儘管如今的抗議學生不需面對徵兵,不用承擔因拒絕服役而坐牢的風險,但不少參與者都是持學生簽證的國際學生,一旦被捕,可能面臨被遣返的後果。這是 2024 年更多元、更「國際化」的抗爭者必須考慮的。
更讓人回想起 60 年代反戰抗爭的,是現役美國空軍飛行員布許奈爾(Aaron Bushnell)今年 2 月的自焚行動。2 月 25 日,布許奈爾選擇在以色列駐美大使館前自焚,抗議美軍和以色列軍方針對巴勒斯坦人的暴行,並透過 Twitch 直播整個過程。直播影片中,布許奈爾先是說道「我不再是種族滅絕的共犯了」,隨即點燃自己,大喊「解放巴勒斯坦」,直到倒地不起。布許奈爾送醫後,於 27 日不治身亡。
作為現役空軍,又是白人男性,布許奈爾的自焚吸引了眾人目光,也讓世界看到美國社會在以巴問題上的巨大分裂。連《紐約時報》在報導時,都要特別強調布許奈爾「種族滅絕」的用詞,是「以色列在加薩的軍事行動的反對者用來描述這場戰爭的語言」。校園內外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們,則舉辦守夜活動,紀念布許奈爾和在戰爭中喪生的加薩平民。
哈佛學生在一篇刊登於校園報紙的評論中寫道:「將近 60 年前,在布許奈爾為巴勒斯坦人民犧牲前,一個名叫諾曼 ‧ 莫里森(Norman Morrison)的人為越南人民做了同樣的事情。」莫里森是美國反戰運動者,於 1965 年 11 月 2 日在五角大樓前自焚,抗議美國介入越南戰爭。
作為最極端的抗議形式,自焚仍在不斷重演,一如人類歷史上的戰爭和暴行。

以巴問題和大屠殺的記憶政治
事實上,在布許奈爾之外,還有另一位以自焚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士,卻幾乎沒得到多少關注。2023 年 12 月 1 日,一名舉著巴勒斯坦國旗的示威者,在亞特蘭大以色列領事館大樓外自焚。除了事件當天的新聞外,主流媒體沒有再報導過這件事,自焚者的身分至今仍然成謎,只知道是名女性。
幾乎可以確定的是,布許奈爾將會被歷史記住,無名女性自焚者不會。這將我們帶到了以巴問題的核心:我們該記得什麼,我們該如何記憶。
1948 年 5 月 14 日,在經歷二戰期間德國納粹對猶太人實行的大屠殺後,猶太民族主義者在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土地上,建立屬於「猶太人」的國家。打從一開始,猶太人在二戰期間經歷的苦難和以色列建國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在某個意義上,猶太大屠殺(The Holocaust)是獨特的,但不是由於手段、規模或殘忍程度,而是因為猶太大屠殺是人類歷史上最被記憶的大屠殺。
美國猶太裔政治學者芬克斯坦(Norman Finkelstein)生於 1953 年,父母為納粹集中營倖存者,父母的親人大多死於大屠殺中。芬克斯坦於 2000 年出版極具爭議的《大屠殺產業:反思對猶太人苦難的利用》一書,主張在 20 世紀中後期,以美國為主的西方世界媒體逐漸生產出一整套大屠殺論述,將猶太大屠殺形塑為獨一無二的苦難,以合理化美國和以色列的軍事行動。
關鍵轉折點是 1967 年的六日戰爭,以色列在短短 6 天內大敗埃及、約旦和敘利亞聯軍,取得包含加薩走廊、約旦河西岸的大片土地。以色列在戰爭中表現出強大實力,讓美國意識到支持以色列能在中東建立一個牽制伊斯蘭國家的親西方政權,兩國因此形成軍事同盟,美國媒體如《紐約時報》開始推銷大屠殺論述。
在 2001 年《大屠殺產業》平裝本前言中,芬克斯坦給了一組數字:1999 年一整年《紐約時報》一共刊出 273 篇提及猶太大屠殺的文章,卻只有 32 篇文章提及非洲(順道一提,盧安達種族滅絕發生於 1994 年),由此可見西方世界對什麼苦難值得記憶的偏好。
退一步來說,記憶猶太大屠殺本身沒有任何錯誤,問題在於,對過往苦難的記憶,是否限制了我們看見當下的其他苦難、以及理解它們的方式。「種族滅絕」一詞是否只能留給作為受害者的猶太人?猶太人永遠不可能是滅絕其他種族的加害者?「種族隔離」是否只見於上個世紀的南非,而不會發生在此時此刻的以色列?
如同歷史上所有抗議行動,這是一場關於如何理解、如何記憶的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