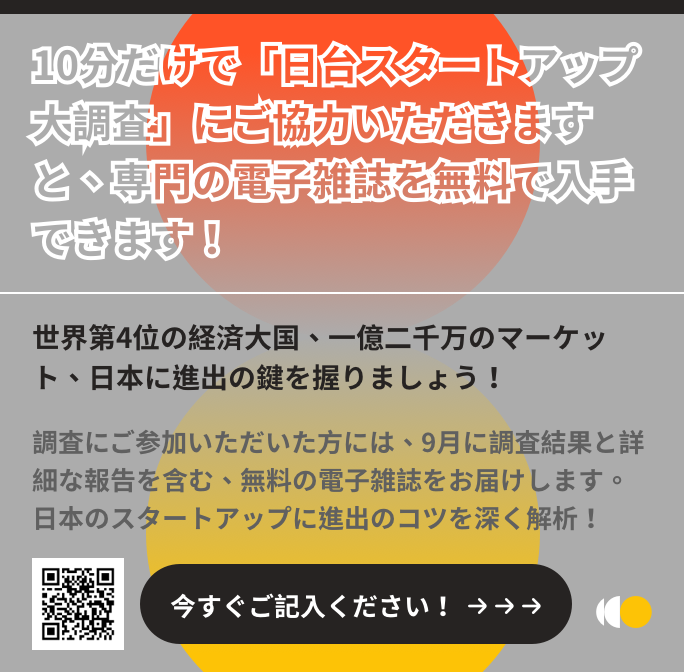安倍晉三來自一個顯赫的右翼政治家庭,青出於藍的第三代。
安倍家族面對的是二戰後的日本政治框架。戰敗後,日本在美國引入的憲法下,當時日本首相吉田茂接受日本實際上並不完全獨立,在美國軍隊的護衛下自身只維持輕武裝,與美國結盟專注於經濟發展。在吉田主義的安排下,日本不會成為一個真正擁有自己權利的大國。
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是戰犯,但並沒有受到審判入獄,在美國佔領結束時,岸信介重新進入政界,1957 年成為首相。安倍家族一直致力於推翻吉田主義的妥協立場,修改憲法並取消限制,期盼讓日本再次成為一個成熟的大國。
作為保守派右翼政治家族,在 2010 年代以前,安倍家的路線並不容易得到世界的認同,在東、西方主流媒體製造的二戰後國際關係共識中,安倍所屬的日本右翼「份子」,是一群好戰的麻煩製造者,是挑起戰爭的日本軍閥主義的溫床,在政治正確的對立面。
中國崛起,賦予鷹派安倍政治正確的空間。
俄羅斯和中國,使得日本右翼保守派得以走向政治正確的光明位。
兩個日本近鄰強國,都由獨裁領導者取得長期統治基礎,比起歐美對北韓的關注,日本對於普丁的法西斯主義,和習近平繼承共產國際赤化全球擴張的企圖,明顯更警惕和小心。
2013 年,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在第二期時提出美國「重返亞洲」的說法,接著習近平就推出「一帶一路」向全球投資的大戰略。也是在同一年,安倍成功在日本政府架構中增加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顧問和秘書處,使得日本自衛隊三部門之間的協調和總理辦公室的決策集中;同一個時間,安倍帶領日本積極加入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談判,並逐漸成為 TPP 談判中,最活躍的主導者。
安倍一點一滴地,顛覆二戰後日本自外於國際紛爭的保護主義傳統。
於是,2015 年,他成功推動內閣重新詮釋日本憲法第九條中有關自衛隊的,日本軍事定位從行使日本「自衛權」,變成可參與盟國共同防禦軍事行動的「集體自衛權」;為了展現日本「共同保衛」的決心,因此,國防預算也從 1976 年限制在 GDP 的 1% 限制中正式掙脫;目標是在 5 年內達到 2% 以和北約國家水準一致;這為隔年安倍對國際社會喊出的「開放與自由的印太」奠下良好的談判基礎。
印太戰略,在北約的東方連接起一道太平洋到印度洋的綿長戰線。
以北約國家的國防預算為目標基準,安倍清楚地向世界宣示要帶領日本重新站上國際舞台的企圖,他也透過 TPP 談判積極拉動東歐跨向亞洲的新國際聯盟戰線;以「民主制度和開放市場價值觀」的倡議者定位,成為聯盟領導人之一。
在修改日本自衛隊在憲法中的適用角色時,安倍向媒體明示,他必須讓日本武裝部隊有能力,去應對台灣周圍不斷提升的潛在衝突。換言之,安倍面對習近平可能長期統治的中國,他心中已經預見戰爭的可能,也毫無猶豫地為此做準備。
在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疑慮下,安倍的路線一直充滿爭議,然而,他非常巧妙的在美國逐漸意識到中國不會隨著經濟成長而民主化後,將他的印太戰略打造成一個華盛頓「難以拒絕的提案」;連結東歐的北約到東北亞,使具有主動軍事能力的日本,成為美軍在太平洋具有共同利益的強國,並透過美國的力量,向西南太平洋與印度洋延伸聯盟戰線。
是軍國主義復辟?還是迎向赤色中國稱霸的新時代?
面對潛在的國際政治衝突,安倍採取極端的實用主義路線,不屈服戰敗國的政治正確,澳洲前總理陸克文說,安倍是 50 年來日本最重要的政治領導人,他「改變了日本戰後的政治身份、外交政策角色和戰略使命。」
怎麼面對獨裁中國霸權崛起的新時代?安倍主動向世界發出了提問:「經濟成長能自然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假設已經被現實否決,我們是否必須正視戰爭的風險正在提高的事實?
日經亞洲 Nikkei Asia 的評論說,安倍把「把世界分為打仗的政客和不打仗的政客」,而且「將自己定位為,為正確的事情而戰的政治家。」
高度行動力和現實主義,是安倍參與國際政治的風格,陸克文這樣形容他的外交收段:「安倍不相信囤積政治資本;他相信使用它。」(經濟學人)
用商業市場的資本邏輯來翻譯這段話,意思是說,安倍是很敢投入資本以累積更多資本的創業型資本家,也就是說,安倍是開創事業型的政治家。
生在這個時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治家?
安倍這樣敢於挑戰政治正確的政治工作者,是我們所期待的嗎?
更具體的提問是,身處在亞太地緣政治衝突的核心位置,台灣人需要什麼樣的政治家,帶領我們度過這個核戰邊緣的衝突時代?
左派媒體例如紐約時報,對安倍這類對衝突毫不猶豫立刻整裝備戰的政治路線,採取批判的態度,也建議現任日相岸田文雄應該在保有安倍為日本撐起的國際舞台上,採取不同於安倍的路線,開始與北京的友善對話。(紐約時報)
生在這個時代,安倍這樣的政治家為日本和亞太地區定義了一個類型的腳本;那麼,台灣現在和未來的政治家,正在為台灣和我們所屬的亞太地區,提出什麼樣的腳本設定呢?
至少,我們可以先辨認,誰是那種只願意囤積、而不願意使用政治資本的政客是誰。
透過我們的選票所獲得的政治資本,若只用來為個人或黨派利益囤積,而不用來為衝突時代提出回應的,不可能會是領導台灣走出新局的政治家。
至於那些願意行動的政治工作者,誰能稱為政治家、獲得我們的倚託?
看他們是否務實的勇於面對這些命題:
- 台灣與川普退出後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TP),是什麼樣的關係?我們要以多高的積極度、多務實的彈性,參與這個新亞太戰略架構?
- 在美、中的霸權衝突中,台灣的國家利益是什麼?如果不是親中或親美的二擇一,那麼是否能提出一個具體可供國際社會檢驗的提案?
- 在 CPTTP 和美國印太戰略、中國的一帶一路國際局勢下,台灣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策略定位應該是什麼?
- 台灣應該要修憲嗎?如果要修,應該怎麼修,才能讓台灣走出在新世紀安身立命、得到國際社會尊重看重的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