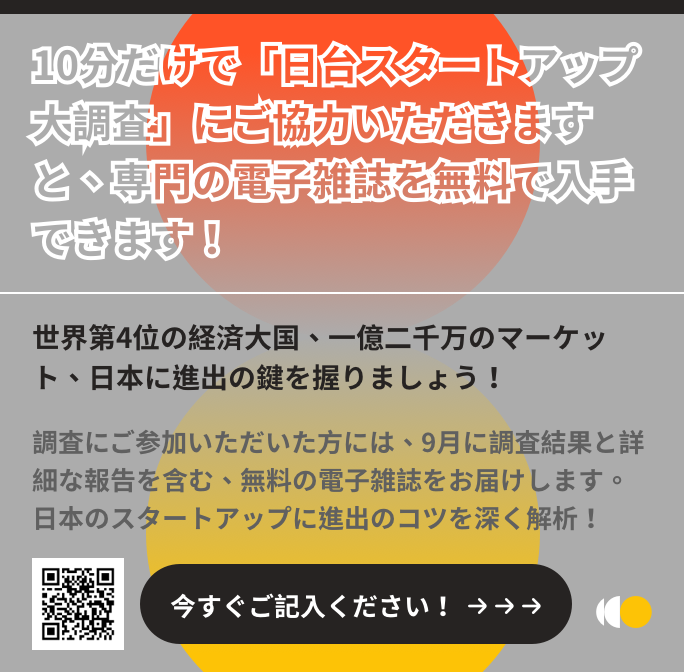初見阿富,身材高壯、談吐得宜,若不是他敞開心防談及過去,很難把他和過去那段將近10年的荒誕青春聯想在一起。
曾經,阿富出生在經濟還算寬裕的家庭,父親經營中古車行、母親從事金融業,幸福童年卻在升上小學後逐漸變色。父親因嗜賭無心打理事業,母親為了另一半的債務疲於奔命,家中爭吵取代歡笑,親子關係越來越疏離。升上國中後,阿富被爸爸安插到台北市數一數二的明星學校,跨區就讀的不適應、成績才是一切的升學主義標準,把阿富一步步推向不歸之路。
在學業與家庭上都得不到關心與肯定的阿富,只能轉向尋求同儕間的認同加入陣頭。阿富說:「那時候其實沒有考慮太多就決定參加(陣頭),因為在學校一直處於高壓環境,特別我又顯得格格不入時,常會有意無意被針對或排斥,很多時候別人多看一眼或多說二句,就讓我不想安分的待在學校裡,承受外界的異樣眼光或師長責罵,轉而尋求外面的支持與陪伴。」
“如果爸媽沒辦法給我完整的家庭,我為什麼要給他們一個完整的小孩?當時以為自己有賺錢能力,或許就能解決家裡總是為錢爭吵的狀態,結果反而給爸媽添了更多麻煩”
接觸陣頭是阿富人生轉變得起點,但追根究柢,當時的他除了想找到類似家的溫暖外,更大的初衷是希望能早點幫忙賺錢,解決家中的紛紛擾擾。講義氣、能打又聰明的阿富很快就被黑社會吸收,當車手、詐欺、販毒走向沉淪,販毒的同時自己也染上毒癮,經常挖東牆補西牆,最終不但沒幫家裡解決問題,反而給爸媽添了更多麻煩。
從國一第一次碰毒到走向成癮,過程中,阿富曾2度進出少觀所,而真正讓他醒悟的關鍵,是直到滿18歲的成人毒品案。
「當時身上有蠻大量的毒品,因為還有分裝袋與磅秤,這些證物在司法系統中有很高機率會被認定是販賣未遂,檢察官當時語帶恐嚇告訴我成年犯持有二級毒品的刑期至少5~7年,讓我真的被嚇到了!」在案件調查審理過程中,阿富甚至做好「跑路」準備。
“很多少年沒意識到犯罪的嚴重性,用逃避方式去解決問題,好像沒看到就沒事,等到真的想回頭了,重新檢視自己,才發現有龐大的債務等著你”
在等待法院判決期間,阿富收拾包袱躲到台中阿公的家,他坦言:「我很刻意和台北的生活與交友圈、公司(幫派)斷聯,如果最後判決結果太重就準備跑路,一方面也想給自己留一點後路,看看有沒有可能往好的方向走。」脫離昔日交友圈,阿富在台中除了幫忙照顧中風的阿嬤,剛開始也會陪阿公下田,不想讓自己太閒胡思亂想,還在飲料店找了一份兼職工作。
最後判決結果出爐,阿富幸運逃過一劫被判戒癮治療,必須定期到台北市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驗尿,然而重新回過頭來檢視自己的人生,阿富這時才發現,過去的荒唐歲月,七八次被警方抓到持有三級毒品K他命的行政裁罰,讓他年紀輕輕就已累積超過30萬元罰金。
「很多少年跟我一樣不見棺材不掉淚,總是用逃避方式來解決問題,好像沒看見(罰單)就沒事,畢竟多數出來混的人根本不會回家,都是家人在收罰單,既沒看到生活上又沒有任何不方便,就忽略其嚴重性,直到想要重回正常生活,再去一一檢視有哪些事情必須去處理時,才赫然發現早已累積龐大債務在等著你。」阿富語重心長地說。
“沒有一個空間可以真的讓人更生,過去的我給社會造成了一些傷害,我想要彌補,幫助那些曾經被我帶壞的囡仔伴 ”
即使努力想變好,但接踵而來的生活、債務壓力,一度把阿富壓得喘不過氣,過程中,他也深刻感受撕不去的標籤。
「跟打工的飲料店老闆變熟後,我不想一直騙他,才告訴他我有案件在跑法院,沒想到說完後,原本一周有5天排班變成只有一二天,當下其實很受傷,畢竟我在工作上並無重大缺失,從沒少過錢或被客訴,當時不只需要賺錢,更希望讓自己的生活有重心,卻是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社會上並沒有一個空間可以真的讓人更生。」阿富說。
現實的挫折雖讓人備感無力,但在阿富的蒼白少年時期,卻仍然有一群不放棄他的社工、保護官與助人工作者,為他撐起一層層保護傘。在他18歲生日當天,過去在少年服務中心接觸的社工送了他一個生日蛋糕,讓長久以來缺乏關愛的少年心中注入一道暖流,阿富回到台北後原本跟父親搬到信義區山上租屋,打開家門周邊都是墓仔埔,也是保護官看不下去,幫忙找尋安置機構,白天阿富可到更生少年保護協會旗下的中繼職場「未來咖啡」打工,晚上回學校念高中進修部,下課後再回到安置機構。
一路參與的更生少年關懷協會主任陳彥君強調:「民間社福機構的好處是我們可針對個案提供各種彈性,以阿富的案子為例,我們會邀請孩子的保護官、家長或社區資源,把相關資源找齊,共同討論如何分工,拜託學校輔導老師多幫助孩子,讓他們能重新適應學校生活,下課後來我們這邊,讓孩子的時間不要是空的,一旦有空的就很危險,靠合作網絡才有辦法拉住一個孩子。」
當然和家人之間的情感修復,也幫助阿富解開生命中最重要的結。陳彥君透露,當時協會邀請父子參加德國海尼格學派的「家族排列」課程,「這是後現代戲劇治療,又被稱作德國的觀落陰,利用共時性原理來投射爸媽當初的想法,先解開阿富爸爸心中的結,讓他理解孩子要的是愛不是錢,父子倆才有換位思考的可能性。」透過從源頭梳理,也讓阿富明白不必再親子關係中選邊站,即使父母最後選擇分開,自己也可以同時擁有爸爸與媽媽的愛。
一次又一次被司法社政與社福單位接住,喚起阿富心中最柔軟的一塊,甚至立志將來也要投入社工領域,成為助人工作者。但問阿富為何會有這樣的起心動念?他則直言是出自於揮之不去的愧疚感。
「我自己回到比較正常的生活狀態後,有讀書也有穩定工作,反而意識到那些當初因為我而碰毒的囡仔伴都回不了頭,不論我如何軟硬兼施都沒辦法......」阿富自責地說:「過去的我給社會造成了一些傷害,我想要做出彌補,不論是那些曾經被我帶壞的同伴,或是幫忙其他跟我依樣走錯路的青少年,畢竟能回頭的真的是少數中的少數。」
“司法少年的人生像走一條蜿蜒的山路,誰不是起起落落摔倒多次,能成功回頭的真的是極少數,最怕的是有些人明明想變好,卻找不到可幫助他自立復歸的資源”
找到人生方向後,阿富白天在未來咖啡打工,空班時利用協會的公用電腦準備大學社工系推甄資料,協會實習生還幫忙模擬面試,甚至還出動志工陪伴他到各地考試,最後成功錄取多間公私立大學。陳彥君笑說:「由此可見改變的力量有多大,只要想完成一件事情,好像整個宇宙都會幫助你。」她始終難忘阿富告知錄取理想校系時閃閃發亮的眼神。
如今,阿富不僅和家人和解,也有份穩定正職工作,可逐步償還司法案件所累積的債務,年初還和父親一起旅行,彌補過去空白的親子共處時光。
他有感而發地說:「司法少年的人生像走一條蜿蜒的山路,誰不是起起落落摔倒多次,我雖然受了傷但至少還活著,就讓這些傷痕成為改變的能量與動力。」當主流價值都在追逐成功的同時,阿富更關心那些跌出安全網絡的人,希望能夠過社工領域的學習,裝備足夠的知識與技能,當那些昔日兄弟需要幫助時,自己隨時都在, 「最怕的是有些人明明想變好,卻找不到可幫助他自立復歸的資源。」